【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白云怡 谢文婷】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今天,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与不确定性,已成为各国政府、企业及个人的共同课题。日前,《环球时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央行前行长斯蒂芬·波洛兹。在波洛兹看来,人口老龄化、债务累积、收入不平等、技术进步和气候变化这五种“经济构造力”,就像地质构造力一样,不断变动、积聚,正在对全球形成影响深远的“经济地震”。

“经济构造力”
环球时报:您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下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中提到,有五种“经济构造力”——即人口老龄化、债务累积、收入不平等、技术进步和气候变化——正在重塑全球经济。能否向我们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结论,这几种力量将怎样重塑我们的经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变化?
波洛兹:我在这本书中把上述几种力量称为“经济构造力”,是因为它们总是在变化、运动,而且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它们的——这就像是地质构造力,当它们集聚并发生碰撞时,就会发生地震。事实上,在19世纪全球大萧条、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金融危机时,这些“经济构造力”都曾扮演过重要角色。
今天,这五种“经济构造力”都在增强:全球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收入不平等达到历史高点并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债务不可持续,气候变化的影响每天都在显现。我认为,随着这些力量相互碰撞,未来可能有更多“经济和金融地震”。因此,个体需要做更多准备,比如我们作为个人可以在财务上比以前更保守一些,并不断学习新的职业技能以应对变化,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灵活适应能力做更多“投资”。
环球时报:您在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可能带来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我们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就业问题?
波洛兹:历史上我们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芯片。每一次新技术都会摧毁许多工作岗位,但同时它们创造出的岗位数量最终超过了消失的岗位数量。许多新出现的工作岗位是此前人们很难想象到的。问题在于,新岗位的诞生需要时间,可能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感到很大的压力。
另外不要忘记,新技术会创造巨大的新财富,一些人失去工作的同时,另一些“大赢家”收获巨大。这些“大赢家”可能是开发新技术的公司,它们创造和收获的财富将在社会上被广泛地消费,这意味着新的岗位不仅会出现在新技术领域,也会出现在建筑、维护、服务业等其他领域。
今天,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AI)应用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刚刚开始,这肯定会带来一段很紧张的时期,可能会影响到全球超过20%的工人。这意味着社会需要有良好的“保护网”,以保护处在这个过渡期中的人们,并应当为个人提供跨行业的再培训机会,以便让这个过渡的过程不那么痛苦,并更快地获得技术进步的收益。尽管我们无法阻挡变化的发生,但我们可以让这个过程更平滑顺畅一些。
环球时报:有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今天以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和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不同,它无法像蒸汽机和电力革命带来社会化大生产那样催生出更多岗位需求。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波洛兹: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以AI汽车为例,如果所有货运卡车都成为自动驾驶汽车,那么我们将需要新的人力来维护这些复杂的车辆。此外,我们还需要新的交通控制系统,类似于飞机的空中交通管制(这些都会产生新的岗位),这只是一些简单的例子,实际上新的环境中一定会出现更多我们从未想过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当AI如预期的那样投入到很多应用中,将创造大量的价值,这些价值流入经济中,将推动各个领域的增长。我对此持乐观的态度。
每次技术革命都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然而,有些人可能会被抛在后面,这种落后可能是长期甚至是永久性的,这可能导致政治动荡,以及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我们应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更加下力气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防止社会进一步分裂。
“越是飞在前面的头雁,遇到的风越大”
环球时报:我们也想同您聊聊中国的经济情况。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经济的表现?有声音认为,“中国已经见顶了”,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波洛兹:我不认为“中国已经见顶”,中国可以取得更大的发展。也许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像以前那么快了,但我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任何经济体随着其成熟,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规模的扩大,其增长率都会自然而然地放缓。而且就像成群而飞的大雁那样,越是飞在前面的头雁,遇到的风就越大,国家也是这样,越是发达先进的国家,迎面而来遇到的挑战也就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见顶”了,它完全有可能达到新的高度。
当然,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对中国来说)仍是一项重要工作,不能对此掉以轻心。深度投资、发展教育、加强协作、跨学科研究与开发等,都是保持增长势头的重要努力方向,也是中国丰富的资源和手段。此外,政府还应破除可能阻碍增长和创新的障碍。只要没有这些障碍,我相信,经济发展一定会继续。
环球时报:近年来,中国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并推动绿色转型。您如何看待这一进程?它会取得成功吗?外界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有一些质疑和诟病,您怎么看他们的说法?
波洛兹:我认为,新能源产业正是一个政府应该介入的领域。我们生活在一个碳排放过多的世界,在这方面,市场失灵了,市场没有带我们到达正确的地方。人们开车、购买直接或间接造成污染的工业制成品,造成了空气污染,但没有人为此买单,而每个人却都在为污染和气候变化付出代价。
随着人类的发展,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能源安全对人类至关重要。而绿色产业的发展能够为我们延长能源转型的时间窗口,并在未来几十年延缓气候变化的发生。然而,市场自己没有减少污染或碳排放的动力,所以我们需要政府的介入,去纠正这种市场失灵,这是一个公共产品的问题。当然,有许多方法可以纠正这种失灵,但我认为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以推动整个经济体系进行调整,比如采取对碳排放定价等措施,或对碳排放设定规则,要求企业减少排放,以及推动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
全球化不是黑白分明的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备受关注。您如何看待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未来中美经济合作和竞争的趋势是什么?这会为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波洛兹:我相信中美两国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未来都密切相关。就像刚才说过的大雁的比喻。很明显,雁群是一起向前飞的,国家也一样,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最佳方式。我们有许多旨在推动国家间合作的论坛、组织或机制,它们曾在危机中发挥过良好的作用,但在很多其他时候,它们的效果并不那么明显。
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发生在中国商人和美国商人之间。我认为多年的生意往来让这些人彼此了解,且彼此有好感,这种关系其实比政治关系要更强大。它们由共同利益驱动,而非政治原因。我希望这些联系能继续给我们带来好处,克服一些政治化的干预,成为未来成功的基础。
我今天最担心的其实是不确定性。正如我们在采访开头讨论过的,这些不确定的经济力量让我们的未来更加不稳固。我认为今天的政治也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它正在减缓商业投资,放缓了整个雁群的前行速度。这对我们个人也不是好事。我们应该致力于减少这种政治不确定性。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全球化的前景?在新冠疫情后,“近岸外包”兴起,比如许多企业把其供应链从中国和东南亚转移到了墨西哥。您认为,全球化的时代是否正在终结,区域化的时代是否正在兴起?
波洛兹:全球化永远不会结束,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趋势。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很久以前就教导我们,将劳动分工成越来越小的部分,能提高生产专业化的程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就像在当今的经济生活中,我们不会再自己去洗衣服,不会再自己去亲自种菜,我们会去干洗店和杂货店解决这些事,而有另外一些人专职从事这些事务。这也让我们得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全球化是把类似这样的小事扩展到了全球层面。两百年前,要做到全球化是困难的,因为牲畜和船只的运输能力达不到,但今天这些已不再成为问题,国际贸易也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确实,新冠疫情期间,许多供应链被中断,因为疫情让我们看到,供应链太分散会存在风险,全球化并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今天发生的供应链重组实际上更多是由“首席风险官”来推动的,而不是首席财务官,前者专注于风险管理和防范重大问题的出现,而不是减少成本和提高效率。
我认为这种关注焦点的转移,其实是全球化的一次再平衡,新的平衡可能和以前略有不同,但全球化将继续存在。全球化不是黑白分明的,它是不断地再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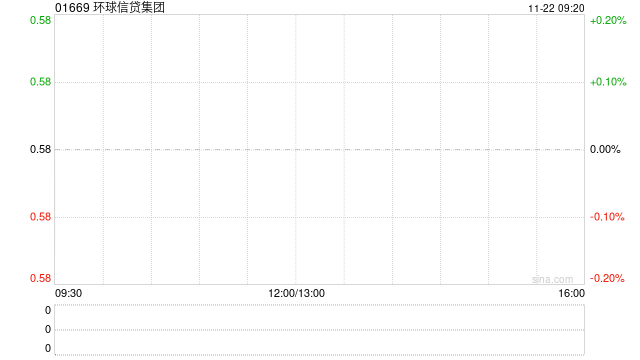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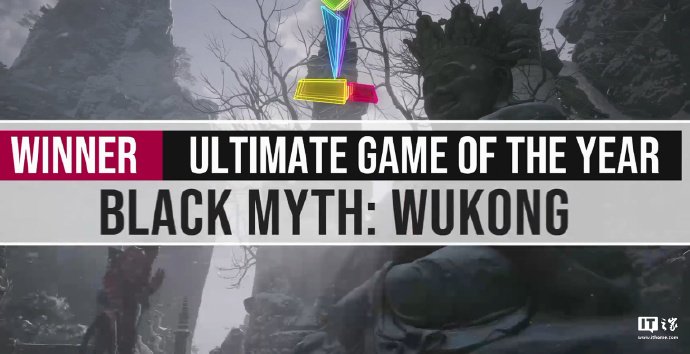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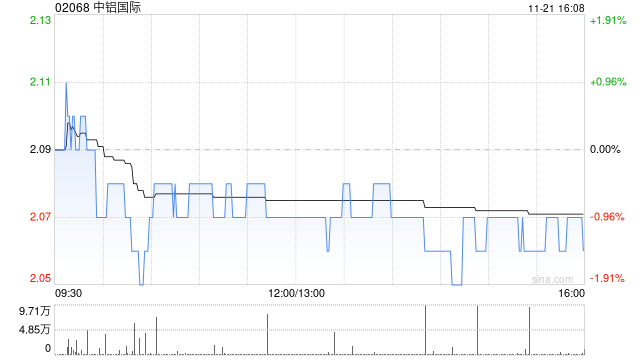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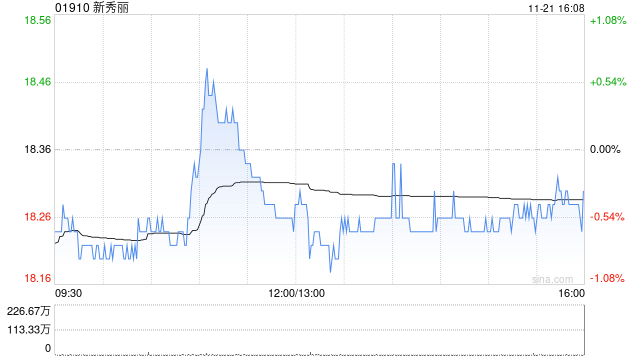





发表评论